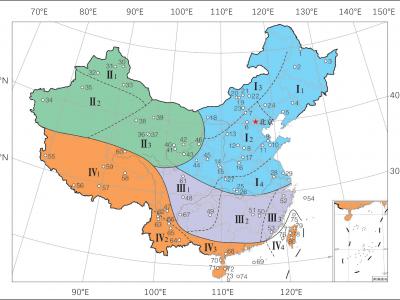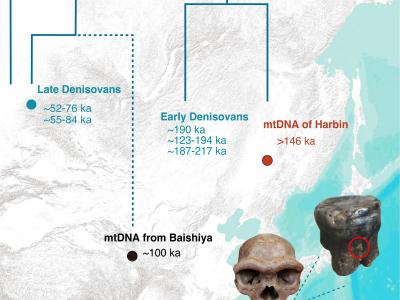修个路也能挖到恐龙蛋 这座粤东北小城堪称现实版“侏罗纪公园”
黄氏河源龙发掘现场照片
2020年6月,河源联新村发现恐龙蛋化石现场。
河源恐龙博物馆陈列的恐龙蛋化石
(化石网报道)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记者黄垚、周颖):9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号刊发题为《修个路也能挖到恐龙蛋,这座粤东北小城堪称现实版“侏罗纪公园”》的报道。
2004年,广东河源凭借10008枚馆藏恐龙蛋化石一举拿下吉尼斯世界纪录。16年后的今天,这座粤东北小城并没有停下发掘脚步,恐龙蛋化石数量逼近两万枚。
执着的“集蛋者”热情不减、数量不断刷新,但修复和研究难题随之而来,解谜需要的时间和努力与日俱增。
沉睡的化石包裹无数生命密码,但科学问题的解答向来无法一蹴而就。
这是一个“抢救”历史痕迹的故事、一个修复碎片信息的漫长过程,更是一个了解远古的窗口,等待我们去认知、解剖,找寻物种进化关联与人类最原始、也最遥远的生命密码。
炸出一窝“恐龙蛋”
早上8点,河源恐龙博物馆馆藏研究部副主任黄志青把草帽和水杯扔上吉普车后座,就向10多公里外的工地开去。6月中旬,派出所的熟人发来微信,说“联新村一工地发现了疑似恐龙蛋化石,你们要不要来看看”。黄志青一下来了兴趣。
到工地后果然没有让他失望,施工爆破的石块里已经能看出明显“端倪”,黄志青打算就地勘察。跟随施工进程,他几乎每天都来工地,在岩壁和石块中找寻蛛丝马迹。
车驶出中心城区,滚烫的阳光炙烤着裸露的岩石,企图唤起深埋地下的远古生物信息。黄志青的思绪一下飘到24年前那个夏天。
彼时距离河源发现第一窝恐龙蛋化石不过几个月。1996年3月6日,在城南南湖山庄工地玩耍的4个小学生意外发现恐龙蛋化石,打破了这个粤东北小城的平静。随后,河源恐龙蛋化石发掘出现“井喷”,一枚枚、一窝窝形状各异的恐龙蛋化石在各村寨、工地“露头”。
“数字每天都在刷新,大家没想到这样的石头就是恐龙蛋。”时任河源市博物馆馆长黄东回忆,之前自己恰巧看过恐龙蛋相关资料,“知道这个东西很珍贵”,就赶紧给市政府打了报告。
一个星期后,河源市政府发出关于保护恐龙蛋化石的通告,明确施工动土时须报请市博物馆派人到现场考察等内容。通告贴遍村头巷口、工地道路以及红砂岩分布的地区。这时人们才知道,曾经在河源民间流传的“神仙脚印”,其实是恐龙蛋化石脱落后的蛋窝。
根据群众和工地发来的线索,黄东带着博物馆工作人员四处“抢救”,单单在河埔大道就捡了800多枚。修路的工人感到惊讶:“原来这就是恐龙蛋啊!路下面不知道埋了多少呢!”
数量之多令人惊讶,且多在山地,黄东咬咬牙用本就不多的经费买了一辆二手吉普车运送化石。随后,黄志青开车载着同事开启了一次次“寻蛋之旅”。河源盆地100多平方公里的红砂岩层,厚度达4000米,到底埋藏了多少恐龙蛋?他们一次次靠近答案,但从未揭开。
“不仅裸露在岩层表面的化石很多,有的山头每层都有,甚至随便施工炸山就能发现。20米高的小山丘一炸开,发现了237枚。”黄东说,“哪怕在河源市恐龙博物馆新馆工地上,都发掘出一窝16枚恐龙蛋化石,至今还有3枚露在馆墙边的石壁上。”
增长几近疯狂。2004年11月,河源市博物馆拥有恐龙蛋化石已达10008枚。次年1月,他们接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荣膺世界馆藏恐龙蛋化石数量之最。
荣光之后,发掘仍在继续。四面八方的线索不断涌来,只不过逐渐从电话变成了微信。“这几年派出所经常来消息,有时候抓捕行动也会带上我们。”河源恐龙博物馆馆长杜衍礼说,“有次在一个毒贩家找到了两窝,我和黄志青一趟趟搬回来;还有次派出所收缴了500多枚,附近居民把水桶借给我们才弄回来。”
多年来,黄志青已经练就了深厚的“目测”功底——在同一岩层,从已发掘的点位用肉眼判断找出另一个发掘点,“胜率”颇高。他的车换了两三辆,发现化石也从“兴奋”慢慢转向了“责任”。但每次开车出门,他总能想起在一个个燥热夏天,穿着背心、戴着草帽意气风发的“寻蛋之旅”。
“当年的通告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年馆藏的化石起码70%都是群众提供线索找到的。”杜衍礼说,在河源,人们对恐龙蛋化石的认知已经“深入骨髓”。
去年7月,河源9岁的小学生在东江边玩耍时发现破碎的蛋壳化石,一眼就认出来这可能和恐龙蛋有关。随后,博物馆在地下发掘出11枚蛋化石,并判定这些恐龙蛋应该属于白垩纪晚期。
目前,河源恐龙蛋博物馆馆藏恐龙蛋化石已超过1.8万枚。这些化石种类丰富,长条形、棱柱形、椭圆形、扁形、圆形等形状各异,规格从1.5厘米至23厘米不等,大多属于白垩纪晚期。但深埋在城市钢筋水泥下和未开发山区的数量,仍是未知。
修复“历史信息”
面对博物馆里像番薯一样码放的恐龙蛋化石,黄东感到最遗憾的是丢失了“历史信息”,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多年来,他像一个疯狂的化石收集者,在每一辆挖掘机的车斗下“抢救”化石,和城市发展速度赛跑。
“以前没有那么先进的探测手段,收上来单个的化石也不知道它周围地层环境是怎样的,更别说知道这颗蛋属于什么恐龙了。”黄东说,“这种情况下,‘抢救’仍是第一位的,必须为后续的研究留下标本。”
发掘前几年,恐龙蛋化石数量惊人,但迟迟没有见到“龙”的身影。直到1999年龙骨化石和2001年恐龙足迹的发现,远古河源的恐龙生态画卷才徐徐展开。
1999年7月,河源市民林德和在黄沙村的一处荒坡挖出恐龙骨骼化石。黄东立马扩大寻找范围,并带着样本前往北京。经专家鉴定,确认化石为“指骨或耻骨的远端”。当年8月,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董枝明、吕君昌等专家来到河源现场发掘,发现了一块长约20厘米的恐龙肢骨化石。
收获令人意外,但由于经费原因,发掘在不久后暂停。野外经验丰富的吕君昌让工人将部分生活垃圾埋在发掘点,“留个记号”。
近5年后,发掘重启。当初的荒坡早已被夷为平地,发掘点失去了所有位置参照。一半靠记忆一半靠运气,挖了3天,在经费快要耗尽的时候终于挖到了吕君昌曾经让埋下的塑料布。黄志青打电话给黄东报喜,电话那头黄东觉得难以置信,说:“你别开玩笑啊,我这几万块经费都快没了!”
伴随挖掘的是旷日持久的修复。“当时加上临时工不过两三个人,大家几乎都是‘半路出家’从修复恐龙蛋化石学起,最开始就顺着纹路一点点敲下去。”河源恐龙博物馆副馆长袁伟强说。
靠5块钱一张门票收入的博物馆负担不起太昂贵的修复支出。他们只能买硬度大的高碳钢剔针来“对付”包裹化石的坚硬岩石。“硬碰硬”的结果是工具很快钝化,修复工人得不停打磨,并逐渐掌握了打磨蘸水的火候。“我们后来都成了非常熟练的钳工。”袁伟强说。
对他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修复肋骨和头骨。出土的头骨已被压扁,很难判断形状和走向;肋骨细长,断断续续凌乱交错。“走向错了就毁了。”袁伟强说,“在没有电子放大镜的情况下,修复犹如刺绣,精细且缓慢,通常1天也修不了几平方厘米。”
随着修复难度加大,吕君昌到河源进行指导。“我们博物馆在编只有7个人,每年办公经费总共不到1万元,扣去日常开销所剩无几。”袁伟强说,当时为省钱,他陪吕君昌在博物馆附近的金花庙住了一个月,吃饭问题轮流在博物馆员工家里解决。
吕君昌告诉他:“化石修复最重要的是保留有用信息。”条件所限,袁伟强只能用不太精细的工具一点点将“历史信息”剔出来。修复肋骨他花了3个月,修复头骨花了半年。
最终,三具完整的恐龙正型标本得以呈现。经专家研究,这是河源地区特有的一种恐龙,属窃蛋龙类。吕君昌在发表的论文中将其正式命名为“黄氏河源龙”。
随着时间推移,博物馆用于发掘的铁锤换成了地质锤,高碳钢剔针也换成了进口气动枪。接棒修复工作的馆员黄华乐如今在100多平方米的板房里,拿着气动枪像牙医一样,慢慢让化石更加精准地露出本来面目。
但即使工具进步,修复的进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单单修一个直径6厘米左右的圆形蛋化石就需要1个月,6大窝化石整整修了4年。”黄华乐说,这是一项靠毅力的工作,每修出一个化石都是微薄力量积累的结果。
对于慢工出细活,黄华乐并不着急。“每一个阶段需要的都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和科学态度。”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强认为,若保存条件不具备,标本修复出来反而对后期研究是种破坏。“技术力量欠缺是各地博物馆都存在的问题,加上古生物专业性很强,不同的标本在保护要求上侧重点有很大差异。”
黄华乐说:“历史给我们留下信息,我们要想办法把它挖出来,等技术更加成熟时,更多的谜题才会慢慢解开。”
杜衍礼说,河源恐龙博物馆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资料系统。每一个恐龙蛋化石的尺寸、重量、地点和层位等信息都清晰记录在案,像一串串加密符号,等待未来一一破解。
恐龙“产房”与绝灭之谜
地层犹如一本天书,每一页都等待我们仔细翻阅和解读。作为地层中携带独特信息的恐龙蛋化石,它们已不再是单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展品,而是研究恐龙演化、绝灭等的重要样本。
尽管我国恐龙蛋化石资源丰富,但学界的相关研究并不多。直到恐龙蛋化石研究专家赵资奎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分类和命名体系,方向才逐渐清晰。
对于河源发掘出海量恐龙蛋化石,专家认为这和其古地理环境有关,大规模施工也为发现化石提供了契机。恐龙集群产蛋需要一定湿度,湿润的场所能给恐龙提供更加舒适安全的产蛋环境。聪明的伤齿龙蛋壳厚度不到1毫米,它选择将尖头一端插在土壤中固定,减少“风吹草动”对孵化的影响。
筑巢产卵行为是恐龙蛋化石研究的重要部分。河源出土的化石种类多样,其中不乏蛋窝结构完整的窃蛋龙蛋化石。窃蛋龙的蛋窝呈现圈层结构,通常像时钟一样一圈12个,上下垒几层。拥有双输卵管的恐龙是一次产下两枚还是多枚、一个周期产下一层还是多层,以及窃蛋龙为何选择如此规律的排列方式,我们还不得而知。
“以一窝3层共36枚的窃蛋龙蛋为例,恐龙若一次产4枚需要9天、一次产2枚需要18天。我们正在从数学和力学的角度去验证,因为这能反映恐龙腹腔里到底能放多少枚蛋的问题。”王强说,目前研究大致可以判定,恐龙产蛋和生活区域是分开的,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有的地方“有龙无蛋”或“有蛋无龙”。
和其他地方在细软土壤中发现化石不同,河源的恐龙蛋化石主要从粗糙的红砂岩中出土。“我们在全国跑了这么多地方,这是唯一一个特殊的粗糙‘产房’,所以河源的产卵环境比其他地方更为恶劣。”王强说,这就为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从理论上拓展了恐龙的生存范围,也反映出这个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性。
在面积不大的盆地里,河源出土的恐龙蛋化石种类繁多,且从地质时代来看,在我国整个恐龙蛋化石资源中占有上下衔接的地位。但多年以来,大家并没有在近两万枚化石中找到胚胎。
专家解释,在数量巨大的化石中排查本就是浩大工程,且胚胎发育程度不同,在蛋中可见的骨骼多少和大小有很大不确定性,虽可借助CT扫描,但依然很难准确判定骨骼的发育程度。这正是下一步留给研究者的科学问题——尽可能寻找胚胎,探索恐龙和蛋的联系。
目前,全球命名的恐龙超过1000种,我国拥有其中300多种化石资源。王强说:“我们尝试通过古生物学、岩石学、古地磁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等多角度进行综合研究。多学科合作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完善的认识问题。”
包括恐龙蛋在内的羊膜卵,其蛋壳结构是古生物摆脱海洋、走向陆地的典型标志。强大的恐龙“统治”地球上亿年,却在白垩纪末期突然消失。对恐龙的研究并不只是满足人类好奇心,它更像是地球留下的谜题,需要我们艰苦卓绝的探索和努力来解答生存和消亡之谜。
关于恐龙绝灭之谜,专家更倾向于因为恐龙对环境的不适应。“小行星撞击可能只是诱发因素,或者说加速了这个局面。但决定性因素还是物种本身和环境相互不协调、不匹配,造成了被自然淘汰的结果。”王强说。
和恐龙蛋化石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黄志青认为,这是在探索人类的生存问题。“近年多发的地质灾害、气候变化等都是地球对人类活动的感知和反应。我们需要通过研究已经绝灭的物种,来更加深刻地认识我们生存的环境。”黄志青说,“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我们不会成为下一个绝灭的物种。”